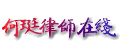“散步”是为了避免暴力
899 人阅读 日期:2009-01-18 18:23:25 作者/来源: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发自北京
■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
■中西部小县城里升学、就业机会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多,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那就更易呼啸成众,肆意而为。这在以前的广安、 大竹事件中已有显现,在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中男青年的暴力行为更为突出。为此,我曾提出要关注“县域青年”的命题。
■从我们研究来看,“群体事件”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峰期。可以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数量上甚至还会继续增加。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瓮安、孟连、出租车罢运等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为此担心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危险的程度,有人则认为,这只是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先生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并对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了深入研究。
与一般研究人员不同,单先生多次亲赴事发现场做实地调研。熟悉基层调查的社会学方法,能驾轻就熟很快“进入”现场与各方面的人士沟通,使得他能够在掌握比较真实全面的材料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较为理性而客观的深度分析。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问题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
错误的“乐观”与“悲观”
南方周末: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年,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单光鼐:目前对于群体性事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两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一种认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强大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人民警察,闹事也就是闹闹而已,成不了大气候,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种呢,认为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物质生活丰盛了,人的思想却乱了,贫富差距大了,贪污腐化多了,下岗失业的人这么多,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么多,社会布满了干柴,到处都是火药桶,只差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前一种是盲目乐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轻视,掉以轻心;后一种是悲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害怕,遇事惊慌失措。
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行为,若依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和对制度的扰乱程度四个维度,可以将其排列成一个谱系,那就是:“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就我们的分析来看,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尚表现为“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既不是诉求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的“社会运动”;更不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有党派势力从中作祟的、社会危象频仍的“革命”前夜。海外有媒体渲染的“瓮安起义”、“陇南暴动”,显然是夸大其词。
现有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前几年的万州事件(重庆市万州区一名自称局长的男子与其妻当街暴打挑夫后,引发公愤致使出现群体性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高一些,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四川汉源因移民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有的事件起初是诉求、目标明晰的集体行动,随着其他人裹挟进去,又演变为没有目的而仅是发泄愤恨情绪的集体行为,整个事件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混合体。如前两年的广安事件(因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 大竹事件(因女工离奇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以经济、民生利益居多,且是单一议题,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抗议企业污染环境、追索医疗责任、要求查明亲属死因、抗议客车涨价,等等。
这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大都没有既定的预谋,矛头也大多是指向企业、地方权势阶层和地方政府的不当之处,没有指向中央政府,更很少质疑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南方周末:我在下面经常听到很多老百姓的说法是:中央政策好得很,但一到下面就被县乡干部这帮人搞歪了。
单光鼐:是这样的。我听到和看到的比较一致的情况是,民众信心在从基层、地方、省到中央的排序中呈逐级递增趋势。
这种“上级比下级好,中央比地方好”的心态,是下层群众聚集的观念基础,它影响着民众对聚集事件政治风险和成功机会的判断,从而影响他们诉求方式和行动策略的选择。
一些人遭遇不公,在基层解决不了,除了不断的上访外,往往就会采取尽量把事情闹大的办法,借以让上级或中央了解情况,求得问题的解决。
具体表现在,群体性事件往往援引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2004年,四川汉源的农民因征地补偿纠纷在水坝工地上聚集时, 打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横幅,喊着“拥护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口号。他们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汪洋的到来是欢迎的。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同志到村里与群众座谈,男女老少跪了一大片,企望有“青天”为他们做主。
2008年的新特点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就你来看,2008年与前几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单光鼐:总体来讲,有这么几个新的情况。
一是暴力程度大大加剧。瓮安事件出来后,我心里“咯哒”了一下,它往前推进了一步。我们说瓮安事件是新世纪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标志事件,就在于它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二是在暴力程度加剧的同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和各地的警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理性和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是目前民众诉求有由特殊变为一般、由具体变为抽象,事件由个别地域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苗头。例如,2007年厦门“散步”取得问题的妥善解决后,2008年年初的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和年中的成都市民反对彭州石化项目,参加者都力图借鉴厦门的经验;2008年的出租车事件也明显地从一个地方迅速 向更大范围蔓延开了,且还提出搞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能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
四是信息更为公开,主流媒体也逐渐学会了不讳言“负面新闻”。汉源事件时,地方政府封锁消息,连主流媒体的记者都不让进去。我们当时几次进去也都只能悄悄地进入。2008年瓮安事件时,开始也是把路堵了,把手机信号屏蔽了,后来完全公开了,我就是公开去调查的。
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我想可能一方面是信息更公开 了,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多了,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另一方面就是2008年出了好几个恶性的个体事件,像杨佳案等,让大家觉得好像气氛比较紧张。
我有个基本判断: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几件群体性事件,就轻言它们表明了民众对党和政府存在严重与普遍不满;也不能就此推论出中国已陷入了社会危机,马上就有发生大面积社会动荡的可能。我依然信从这样的结论:“大局稳定,问题不少”。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 “散步”、“集体休息”这样的表达方式?
单光鼐:我们要给民众一个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现在是各地民众自己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方式,老百姓在不断“试水”,一方面,他们希望以这种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力求尽可能做到不违背现有的社会规制。因此创造了“散步”、“购物”、“集体喝茶”、 “集体休息”等形式。这也实属无奈之举。像厦门、上海和成都都是中产阶级维权,相当理性;这次重庆出租车司机是蓝领维权。重庆人是有名的火爆脾气,但仍能做到这样理性,也很不容易。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宽容。厦门散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针对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散步,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在重庆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市委书记薄熙来和行动者直接对话,解决问题;瓮安事件,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群众鞠躬致歉,果断免除四位县委、县政府领导。这些都是政府应对的亮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省、市领导开明、亲民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也证明民众是可以和政府理性互动的,双方都在其中学习民主、学会妥协、学会良性互动。
在很多地方,警察也表现得很克制,无论是在上海、成都和重庆,还是广州、深圳和海南。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就没有抓所谓幕后组织者,只抓了一些砸车的人 ——砸车的人还是要抓的,任何人都不能搞暴力。我跟一些地方公安部门的同志讲,你们下半年出现了很多亮点,你们的应对有了很大长进。
相对暴力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言,“散步”要轻微得很多。我认为,是不是考虑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中,尝试和摸索出一种形式让它制度化,这样一是可以保证群众的合法权利,二是也可以对其规范,使行动保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准则主义许可制”。
从这些年来看,一般和平的方式往往发生在资讯发达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暴力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发生在中西部相对封闭、偏僻的小县城。民众和政府都要理性,要寻求一种妥协、可以让双方接受的表达方式。倘若找不到一种“最好的”,能找到一种“次优的”,也应允许。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发生暴力,双方又能接受,就可以允许尝试。其实,现在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宽容散步,就是为了避免暴力。
南方周末:为什么暴力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县一级的会比较多呢?
单光鼐:我觉得是现在的县域环境有问题。
小县城社会分化远不如大城市那样分明,农民就是数量最大的群体。在长幼尊卑、等级序列依存的社会环境里,往往“强者,更强势;弱者,更弱势”,草根群众遇事容易激活“我们(农民)”和“他们(当官的)”的心理分界。这种心理分界越强烈,官民互动中的怨恨就越明显,草根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就越广泛。况且,小县城里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有无相通,疾病相扶,患难相助”的风气远较大城市盛,凡事一出,四里八乡的血亲、姻亲、邻居、同乡、同学、朋友很快就会聚集起来帮忙。尤其是中西部小县城里升学、就业机会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多,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那就更易呼啸成众,肆意而为。这在以前的广安、大竹事件中已有显现,在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中男青年的暴力行为更为突出。为此,我曾提出要关注“县域青年”的命题。
还有就是,县一级官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改进不大。2008年5月某县委书记为了求群众不要去请愿,四次当街下跪,手足无措的窘态尽显;瓮安事件中,县委书记、县长躲避群众,都不到现场去,反而远离现场;陇南事件时群众也是再三要求见市委领导,但也是避而不见。当地有干部讲,事发当天,如果某书记出来见一下群众,事情也不至于演变成这个样子。
不要过度“政治化”解读
南方周末:目前国内外都有一些声音将中国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成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你怎么看?
单光鼐:不要过度政治化解读目前的群体性事件。世界各国,无论是何种政治体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群聚事件。如果一个政府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群聚事件或社会抗议就会转化为积极因素,相反,就很容易转化为社会不稳定的消极因素。
一些事发地的政府往往倾向以“敌我矛盾”来定性群体性事件,把本是经济、民生利益诉求的事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成为一些官员普遍的思维定势,面对群众的集体行动,总以为是和政府作对,是反政府行为。考察2008年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思维习惯时有表露:凡事发生,还未及细查就匆忙定性,如“有组织、有预谋”;或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或称“有黑恶势力操纵”;或直接称“街头政治 ”。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群众,轻则称之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重则称之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闹事者”、“不法分子”等等。“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类似说法我们已经谈了几十年,那些都是阶级斗争时代语境下惯用的语言和概念,现在再以此来解读群体性事件,往往没有了任何说服力。
过度政治化解读会留下后遗症,其一,容易扩大打击面,制造出大量假想敌人,把自己推到群众的对立面;其二,容易扩大事态,激化矛盾,不利于平息事情;其三,定性过激,往往会引发执法不当,处置不妥,这就容易授人以柄,被海外某些人利用。地方政府之所以习惯于政治化解读,对事件做简单化处理,其实往往是为了推卸自身责任,为自己采取强制措施寻找合法性。
对群体性事件做过度政治化解读,往往也是海外一些人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社会形势进行恶评时惯用的说法,比如,他们经常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暴动”,将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渲染为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政治对抗。他们每每以此夸大每次群体性事件当中群众的死亡人数。经我们核查,海外媒体历年来对群体性事件报道 的死亡人数很少准确。因此,对“过度政治化解读”,我们应持审慎的态度,小心掉入人家的话语“陷阱”。
从去年年初的上海“散步”,年中的成都“散步”和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集体休息”这些事情来看,是老百姓自己在淡化政治色彩,自己强调自己没有组织性,在寻找非暴力的方式,寻找和平表达的可能性。
当然,不过度政治化解读,并不表示对此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加剧的倾向。
“群体性事件”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南方周末:你判断中国群体性事件可能加剧的依据是什么?
单光鼐:一般来说,“群聚事件”在“开放”尚不完全、“封闭”尚有存在的过渡阶段较多发生。一方面,社会相对“开放”、宽松,群众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另一方面,社会相对“封闭”,民众诉求不能自由表达,缺乏渠道,只好采用“群聚”抗议的手段。因而,这个时期“群聚事件”会频频发生,成为常见的“非正常行为”。
研究群体性事件必须重视民众的社会心理。“群聚”常常发生在社会结构扭曲、社会关系紧张或任由单个的个人孤立地面对强大的社会这样的一些状况下。
我在万州、汉源、池州、广安、大竹、瓮安等地亲身感受和体会到农民、移民、下岗失业工人、低收入者、贫困人口等的牢骚、焦虑、无奈、疏离等情绪,听到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对官员腐败的抨击,对官民关系紧张的表述,对富人、尤其是为富不仁的富人的仇视。应该看到,这些情绪一时还不会消除,有时甚至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社会心理上看,民众烦躁、焦虑、不安的心态还会持续下去。因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使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心理感受。
从我们研究来看,“群体事件”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峰期。可以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数量上甚至还会继续增加。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南方周末:除了数量可能增加外,还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单光鼐:另一个可能的发展趋势是,组织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集体行为要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条件是,必须有明确的诉求目标,必须能持续地“拖”下去,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为此,群体内必然产生“组织化”的强烈欲望和内在冲动。
万州、池州事件由于没有组织进行组织、动员,抗争性与动员力都很差,“乌合之众”起哄、胡闹一通,便散开;但是,我们从汉源、东阳、黄石(因不满撤市改区,湖北大冶市发生了到黄石以冲击党政机关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等事件看到组织化的端倪。
无论是农村集体维护自身利益,还是下岗、失业工人面临生存危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有了非正式组织或隐形组织的发起、组织和动员。如,发动一连串的联署签名、上访和请愿,创造出一套有力的动员举措,策划动员策略与制造舆论和宣传,等等。
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是很强的,历来有帮会组织秘密结社的习惯和传统。世界各国的体制外群聚事件的发展轨迹也证实,早期的群聚事件往往是组织化程度很低的“集体行为”,倘若社会矛盾、冲突没有舒缓,其后就会逐渐演变为矛盾进一步集中、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由隐形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发起、组织的 “集体行动”,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社会矛盾进一步聚焦于某一问题的“社会运动”了。
我想提醒一句,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09年尤其需要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一些经济问题有可能演化为社 会问题。国外过去的很多事例证明,在经济波动、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有可能增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程度也可能会加剧。
南方周末:对于目前这样的情势,你觉得应该怎样应对群体性事件,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单光鼐:群众和基层政府都要理性、平和,双方都要学会谈判、妥协。群众,要学会“有话好好说”,凡事而动者要坚持“和平、非暴力”; 地方政府,平时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事发时,要在介乎于“压制”与“妥协”之间的灰色地带学会拿捏尺寸。该“柔软”的,“身段还要更柔软”,如对待理性、平和的群众;该“强硬”的,当然也要“强硬”,如发生了打砸烧,就要果断处置,将肇事者拿下。世界各国警察都是这样的原则。
2004年浙江东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调动大量执法人员与当地民众产生暴力冲突,政府可谓形象大损,干警受了皮肉之苦,打砸的民众后来也受了牢狱之灾。三方皆输,没有赢家。2008年孟连事件中,本是胶农和橡胶公司的经济纠纷,政府却站在企业一边,警察帮着企业去对付老百姓,弄成资本和权力结合,又过度使用警力,以致酿成流血。我们一定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西方防暴经验显示,警方愈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示威者,对方通常都会采用更激进的方式对抗。因此,基本上不采取围堵、封杀的策略;相反,往往用软性的办法,给示威者有限的舞台,一定程度的曝光率,似能更有效地防止他们大规模地在市面闹事。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只要有正确的策略、正确地应对,群体性事件是能够得到妥善的防范、引导和处理,向好的方向转化的。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社会也有这样的要求。
<<上一篇文章:2008年十大影响性诉讼
>>下一篇文章:也谈中国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