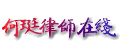李华芳:中国奇迹,还是亚洲戏剧?
930 人阅读 日期:2009-02-04 09:20:11 作者/来源:南方网
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各种新兴阶层的兴起逐渐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系列问题将会导致威权受到挑战,但由于威权之下形成的利益集团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威权发展不会自动消亡。
在中国改革三十年之际,各种带有表演性质的理论纷纷出台,旨在赞扬那骄人的GDP,从一穷二白到“中国奇迹”,为东亚乃至世界都树立了典范。不过这种观点是选择性失明的结果,至少没有看到有两道很大的裂缝在这个所谓“奇迹”大厦的墙壁上。
第一道裂缝是忘记历史所致的。巨大的增长迷惑了不少研究者,使得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的奇迹几乎就是一个基础很差的小学生从个位数的分数进步到及格线的过程。作为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都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人均收入远远低于非洲。而在此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经济更是乏善可陈。这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描绘的局面。
第二道裂缝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不公平程度加深是其表现。以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所提及的,用是不是增进了个人自由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表现,奇迹将会迅速缩水,光彩也将急剧黯淡。阴暗面浮现,但又逼人正视。否则,无聊的文字游戏将会继续编织虚幻的光环。所谓“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名词的共同点是“总产值”,掩盖了分配结果不均以及分配过程不公的事实,也没有说明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只恐怕数字游戏令人迷醉,这种表演还会继续下去。
尤其是第二道裂缝的扩大,可能会使大厦轰然倒塌,而不是一帆风顺发展下去。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东亚各国所走过的道路崎岖坎坷。1968年,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以冷峻的笔触将东南亚打入了贫困陷阱的冷宫。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长、进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以及扩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才能把东南亚拉出贫困的泥淖。即便是在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年代,亚洲也不乏批评者。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这篇被认为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著名文章中,克鲁格曼白纸黑字写下了一个结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问题在于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推广“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非主流。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
近年来,像秦晖、卢周来等本土学者也对第二道裂缝做出了分析。秦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低人权优势”为代价的。不过在卢周来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是改革中获益群体的所得,足以弥补损失,因此只要能够将卡尔多补偿做实,是有希望弥补裂缝的。这种思路,与村上泰亮所谓的“补充性政策”不谋而合。所谓补充性政策是指那些为了应对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以缓和因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矛盾。这些措施要处理的问题包括不平等的扩大、污染、城市化、人口迁移、资产泡沫、腐败、毒品、艾滋病、传统价值观和习俗的沦落等等。
在大野建一看来,东亚的成功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尽管各自的道路不尽一致,但大体上遵循了相似的政策路径,即经济增长政策和补充性政策并举。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各国都大体采用了吸引外资、扩大金融市场、扶持企业、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开发人力资源等措施。村上泰亮认为:一旦预期中的产业开始高速增长,身处这些产业以及相关的人必将经历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态度的巨变……特别是在后发国家,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国民心态,都会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埋下社会紧张关系的种子。这类紧张通常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这种社会紧张关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可能导致政治冲突,最终颠覆经济发展本身。因此对应于经济增长政策,还必须有相应的补充性政策来缓解社会紧张关系。
但在如何实行补充性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呈现出迥异的方案。一种是所谓的“精英治国”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专制政府,采用高压政策启动增长,有可能伴随着计划指令来运行经济,这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紧张加剧。而为了解决问题,专制政府通常采用更加高压的政策,几个回合之后,社会不满将导致人民走上街头,爆发动乱。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民粹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政治参与度的民主政府,当政者把经济利益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但一旦当这种模式无法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时,社会不满就开始积累,大部分的情况下,军事政变将会发生。
这两种模式不仅在亚洲可以被观察到,在拉美也有先例。贫富差距和外部冲击使得拉美生病,一度对中国经济也曾引发会不会拉美化的争论。同时,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萨默斯在一次讲座中曾经提到,在20世纪的经济中,有两个国家值得经济学家注意,一个是印度,还有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有很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人口众多,都处于亚洲,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虔诚或者不虔诚的佛教徒也遍布各自的国家。但他们的增长模式既不同于欧洲北美,也迥异于拉美国家,这会是亚洲的新模式吗?长时段来看,萨默斯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阿马蒂亚·森在最近的一本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的威权模式与印度的民主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两个亚洲大国最终走向不同的道路。
事实上,威权发展模式被不少东亚国家采用,旨在打破贫困陷阱,启动经济增长。这种体制的要点包括: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把经济发展当作国家目标,有一批辅助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而政权合法性来自持续的经济增长。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相关改革开放的实践,是这种模式在中国的表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各种新兴阶层的兴起逐渐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系列问题将会导致威权受到挑战,但由于威权之下形成的利益集团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威权发展不会自动消亡。
但正如前头指出的,威权模式下启动的经济发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就像宇宙飞船达到一定高度,需要将第一节火箭推进器扔掉一样。但实现威权模式的转型并不像扔掉推进器一样容易,甚至在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和寻租集团时,不一定采用了民主的方式。不过那也是短期内的手段,而不是维持下一个模式的长久之计。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外来压力的积累,社会矛盾关系日趋紧张,这些都是威权模式的压力,但能否实现平稳的转换,亚洲各国表演的戏剧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平稳的转轨有可能到来,只不过中国还在十字路口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