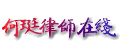当事者忆:1976年打倒邓小平使主席彻底脱离群众
2715 人阅读 日期:2010-11-11 07:35:52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对毛主席是神的信念的最大动摇,就是再次打倒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搞全面整顿。那时我们可是非常热情的,一提起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我们就觉得劲都来了,还很兴奋地说:又要开夜车啦!可是,清华大学刘冰通过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两封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却被毛主席批评了,而且很严厉。[10]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迟群、谢静宜的印象都很坏,就觉得毛主席怎么了?
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使小平同志被诬为总后台,被完全打倒。我完全想不通,是不是毛主席老了?因为我接触到的人都热情地支持整顿,支持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再次打倒邓小平实际上是毛主席彻底脱离了群众,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本文摘自:《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作者: 苏峰,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受访人:王大明,男,汉族,1929年出生。北京市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高等工业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青委东南区委书记。建国后,历任青年团北京市委第五区工委书记、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组长、政策研究室组长,北京市化工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北京市经委副主任、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1998年3月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最大的变化 思想上兴奋
苏峰(以下简称苏):王老,您好!请您谈一谈1978年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王大明(以下简称王):197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也有30年了,我只能从我所在的局部回忆一下1978年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1978年,我认为它应当是拨乱反正大潮的前夕,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涌动、酝酿阶段。当然这个涌动、酝酿阶段的过程,必然会有思想斗争,这是必然的。应当说,这一年是酝酿的一年,是思考的一年,也是斗争的一年。
1978年,在我的印象中,人们还处于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中。说实话,现在我们看来,1978年是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斗争的一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一年。但是当时的我们并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思想上虽有涌动,但是对于上层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也不完全知道,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呢。
全面回忆那段时间,人们还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当中。像我们这些人,就特别兴奋,认为我们可以大干四个现代化了,那时候对于华国锋搞的经济进一步过热,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很兴奋的。
1977年,全国召开工业学大庆的会,我们到大庆去学习了,我带队去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没多久,化工局就开始抓生产,很快就出现了高潮,北京的媒体就报道了化工局的生产热潮,听说还得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和赞扬。这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总算可以干现代化了,四人帮那时候是不让干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
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这批干部的一个情结,再加上1975年小平同志大抓整顿的时候,把这个情结又大大地调动了起来,可惜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要搞十个大庆,四川发现了大型天然气,要把这个天然气引到上海、北京来,我们非常兴奋,大干现代化的热情再次高涨,我们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大庆,干现代化干出个样子来。这是我们当时思想上的一个大背景。
苏:当时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1978年的物质生活没有大的改善,老百姓物质生活的困难都还基本没有解决,但是并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觉得我们马上要干现代化了,这个困难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已经从灾难中走出来了。我印象中,1978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化不太大,但文化生活变化非常大,这个我等一会再讲。较之于文革期间,1978年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很大。物质生活基本还是老样子,但人们并没有觉得苦。我印象中没有人提这个,人们似乎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一切都因为我们要大干四个现代化。
苏:大干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给化工局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围绕大干四个现代化、怎么干四个现代化,北京市化工局已经有小小的改革要求了。譬如说,反对平均主义。譬如说,工厂里面要不要搞奖金?要不要搞计件?怎么样发挥人们的积极性?怎么样使生产秩序更好?这些问题,与文革期间搞平均主义,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东西,不要生产秩序,把生产秩序叫管卡压,都是很不一样的。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已经有改革的要求了。我认为当时下面一些干部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也是有改革要求的。我当时就是积极主张搞奖金,能搞计件的就搞计件。我认为大锅饭、平均主义是不行的,工人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呀。当时化工局下属的厂子众多,一个大橡胶公司下边就有很多厂子,医药公司下面也有很多厂子,还有化工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有机化工厂、化工实验厂,还有出煤气的焦化厂。厂子众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那时候一些更大的、更高一级的改革斗争,我们有一些思想涌动。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围绕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影响生产发展的一些左的东西要打破、要清除。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有不同意见,有思想斗争了,而且还见诸行动了。我记得这一年有一次我去工会作报告,我胆子比较大,说:我觉得可以搞奖金,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就大笑,有的就鼓起掌来。因为这之前,哪有人敢提搞奖金?这是物质刺激!所以,像这些东西,说明我们思想上已经有所酝酿了。那时候,我们这批抓实际生产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搞奖金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真理。不打破平均主义,生产没法上去。
文革前,我在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1]的领导下,经常跑到厂子去,整天在厂子里搞调查,通过调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不可行的。因此,文革一结束,大搞四个现代化,我就觉得平均主义大锅饭必须立刻破除,提出搞奖金也是挑头的。那时候,没有人提搞奖金这类的物质刺激措施,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光学仪器厂提出搞浮动工资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还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阻力。
那时候,青年团、工会有时找我去作报告,都不算正式场合。当时化工局的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像赵庆和[2]等,他们都是长年在基层搞工业的,都很懂得工人的心思,都知道平均主义带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生产无法发展。所以我作报告时,胆子比较大。当时的化工系统隶属于燃料化学工业部,大庆也在燃化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化工系统根据燃化部的部署,比较早地搞了三大讲[3],在批四人帮方面,是带头的。因此,在打破影响工人生产积极性这些东西上,我们思想上禁忌比较少,而且,大家都有股探索的劲儿。不是你想搞奖金,我就想着斗你,不是这样的,而是认为这事必须搞奖金。我印象中燃化部的同志们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把生产搞得快一些。四人帮打倒了,咱们解放了,真是有一种再次解放的感觉。现在没有障癨-了,赶紧抓生产,大干现代化,越快越好!
所以,在初步改革的时候,对这块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当多的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顶多有人抱有疑问,说搞这个可以吗?这和我们过去不一样。没人说这个不能搞,说你搞修正主义。所以,1978年的北京市化工系统大部分人都自然而然地觉得该这么走了,至于要不要搞计件。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对于打破平均主义,大家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不过,当时我脑子里认为计件是最能体现按劳取酬的。
苏:看来当时化工局人们的思想很活跃。
王:是的。北京市化工系统思想的活跃还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关注。当时北京市经委主任叶林、副主任张彭两位同志就经常到化工局来,我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很多同志不时插话发表意见。化工局的干部思想活跃,特别是一批女处长特别能干。叶林说:哎哟,你们化工局够活跃的,女处长们都够厉害的。
我认为那时候我们的活跃不是对两条路线的活跃,是一种该干了、该大干了的思想状态,以及怎么干的探索状态。而且,《北京日报》报道我们化工局大干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后,据说当时还得到了华国锋主席的表扬,我们就觉得更应该好好干了,要在四个现代化上好好往前赶了。这是当时我们的一种心态。
总的来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这些在下面抓实际工作的干部,对更高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认识还没有到某种高度,就处于一种要大干四个现代化的兴奋之中,对于物质生活的一些困难并不太计较。我们还沉浸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从干部到工人,对四人帮的那种仇恨确实是到了一定程度,粉碎四人帮为什么那么迅速,那确实是得人心。四人帮已经把老百姓都得罪透了,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后的再次
被打倒,那确实是犯众臷-了。为什么周总理逝世后,又出现那么重大的天安门事件?这不是谁带头、谁鼓动就能鼓动起来的,这是民心所向。所以到粉碎四人帮,容许批判四人帮了,要大干现代化了,这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在干的过程中,也要探索怎么干得更好、怎么冲破障癨-。在这个冲破障癨-的过程中,有不同意见,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搞路线斗争的做法了。我认为,这就是1978年人们的思想状态。
政治上的关心小道消息
苏:当时您感觉人们都关心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政治上呀,那时候很多人都关心小道消息。
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一个是上面说的处于充满希望的兴奋之中,另外一个我们想得比较多的是为旧市委平反[4]、为天安门事件平反[5]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些干部当中,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压得很沉的。一粉碎四人帮,脑子里就开始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志常在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在这之前下放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聚会,现在我们这些人一回市里,就常去其中一位同志家,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就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们几个就打打牌,聊聊形势。
那时候,这种形式的老同志聚会很多,吃点好的,分析分析形势,在农村待着挺辛苦的,回来当然也就吃点好吃的,稍稍改善一下。在这种聚会上,我们最关心的首先是对旧市委的平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文革一发动,市委就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我们脑子里都想着我们都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衷心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那时候,对文革的根本性否定,还没敢往这个上面想。但是觉得,对北京市委怎么着也应该平反;还有一个,天安门事件怎么着也应该平反。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我们还没怎么想,还不知道大局嘛,想的也是离自己近一点的事情。反正,1978年要求对北京市委、天安门事件平反已经成为相当多干部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
那时候,一见面就问:哎呀,看看现在上面最近怎么样啊?谁有小道消息就贡献出来,就是这样传播小道消息,分析形势,觉得市委和天安门事件早晚得平反,都关心着什么时候平反。包括对刘少奇同志的平反都没有这两个问题议论得多,还没有想到那么高。当时就觉得市委应该为刘仁同志平反,都认为刘仁同志太冤枉了。因为当时,刘仁同志的平反还没有提到桌面上来,上面并没有表态,我们也就只有少数几个知心的人在底下讨论。但是,很多人私底下都讨论为刘仁平反、为市委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来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这些问题已经是广大人民,至少是相当多的干部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苏:一般的群众又议论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我接触的主要是工厂的同志,他们的议论侧重于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因为,有一些工人为这事被当成反革命给抓了。我们化工局在这方面是好的,一个都没抓。保卫处长把电话记录本锁在抽屉里,自己请假,不来了。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就说没钥匙打不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用消极怠工的办法应付了过去。但是另外一些局,有的局都抓了好几十个。这一下子,工人们的议论就很厉害。
当时,我们很多工业局都在市府大楼,局与局之间,因为一些负责人都是当年市委老青年团、工会出去的,之前有一些工作交往,文革期间也都是挨过整的,又都是从下放地回来分到几个工业局的,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所以一有空就串串门、交流交流,于是也就知道这些局里面抓反革命的情况。局里面领导左一点或者胆子小一点的,就抓的比较多。好在那时候化工局的领导班子比较齐心,互相之间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认为最好不抓。
那时候,我曾是办公室主任,扮演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各个处长有什么问题都到我办公室来叨叨,我也就集中起来向局里的一、二把手念叨。他们对我比较放心,认为我比较可靠,不至于揭发他们。我们的保卫处长以前是老公安局的,跟我很熟,他熟悉公安局的一套做法,也反感得很。他就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给他出主意,你把电话记录本锁起来,请假不来上班就是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后,我们就和他们说:这不行啊,人家不在,我们也没钥匙,开不开。于是也就这么拖着,糊弄过去了。一个也没抓,一方面说明咱们顶着干不容易,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我们碰上的那几个公安局的人也不是太较真、太卖力气,一遇见阻力,他们也就不硬来,没和我们对着干。
我们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旧市委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关心旧市委的平反;我们这些人当时大多都在各个工业局,工人们关心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也很关心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我们是最关心旧市委平反的,因为毕竟离市委比较近一点,各个区县的领导、青年团、工会的领导对市委平反的关心度比我们稍低,但比工人要关心得多。我们这些人关心旧市委平反,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呢,我比较幸运一点,刚把处分全免了。
1969年,军宣队刚要我下放的时候,我属于犯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留党察看一年。后来到了农村,过了一两年后,又改成严重警告。再后来我到化工局,粉碎四人帮后,我又申诉,才把我所有的这些处分全免了。时间大概是1977年、1978年。
苏:那您算较早解放的干部了。
王:是的。那时候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有些甚至到1981年、1982年才彻底平反呢。所以我们这批干部对市委的平反非常关心。我算中层干部,解放得稍早。高层一点的干部解放得比较晚一些。我记得我在化工局工作一段时间后,那时候我住在和平里,佘涤清[6]放回来了,王汉斌[7]放回来了,都住在和平里不远。王汉斌分配在一个厂子里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后勤,是排在第十几位的革委会副主任,挺屈才的。我们经常在一块打桥牌,分析分析形势。对于市委一些高层干部,也会偶尔聊一聊,譬如说郑天翔同志怎么样了啊,谁怎么样了啊。谁刚回来,就一起去看看。我还记得佘涤清刚回来的时候,我和张明义[8]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太敢走动,我们属于我们就这样一类的人,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个意思,就去看望刚解放的同志。
1978年总的感觉是,北京市相当多干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刘仁同志平反的要求。刘仁同志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做了大量工作,一定程度上,彭真和刘仁代表着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因此北京市相当多干部非常关心,非常怀念。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文化的大变化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苏:刚才您谈到了文化上变化不小,具体是哪些变化?
王:文化上变化比较大,我记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1978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文化生活有一个亮点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终于打破了!这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看内部电影,哎呀,看内部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干部当中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当时化工局我们这几个人每逢有内部电影,几乎必到。各大部委好多礼堂都放内部电影,还有就是不定哪个单位搞来了片子,就放,于是就发票,要搞到票都是靠关系,于是就有专门的人成天在那里倒腾票。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很喜欢看,化工局工会的同志很积极地去弄票。有时候一弄还能弄到好几十张票,于是一帮子人一起去看。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关于朝鲜一个女谍报员的,连着三集,一演就演一夜,从晚上12点一演演到早上5、6点,在北京展览馆放的。我记得这次是我爱人弄的票,弄到票的时候很晚了,拿到家里来了,大概有十几张票,找谁去呢?一个得找有交通工具的,还得有人爱看,一看得看一夜啊。我就给化工局几个头打电话,他们都是爱好者,兴奋得很,于是要了车到我们家来,把我们接上,一块看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还要开化工局的常委会,我记得这次看完电影后,去赵庆和那里吃了点东西,接着开会去了。挺困的,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开好会。你看,我们那时候瘾头就到这种程度。当时很多人业余时间都在想:现在在放什么电影呀,怎么样搞到票?
苏:都有些什么片子?
王:那时候的内部电影,哪个国家的都有,有日本、朝鲜、南斯繺-夫、罗马尼亚的,连美国电影也有。我现在都记得,一个是《魂断蓝桥》,一个是《鸳梦重温》,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魂断蓝桥》,但知道《鸳梦重温》的不多,我给你讲讲《鸳梦重温》讲的什么故事。它是讲一个英国的贵族军官,在战争中被炮弹震伤,过去的记忆完全丧失了。因为记忆丧失了,忘记了自己的家乡、父母,自己从医院出来的路上,就碰见一个女的,后来和这个女的恋爱了,等于他的生活重新开始了。他们结婚后住在一所房子里,两个人感情很深。后来这个男主人公身体慢慢恢复后,给报社写信找工作,报社也录取了他。他出门准备走的时候,他爱人给他装好了箱子,拿着房门的钥匙。结果他这一出门,叭,又出车祸了。这一撞,他把和他爱人这一段的记忆全忘记了,以前的事情又记起来了,想起自己是什么家族的贵族军官,回到家族去生活了,他的爱人在家里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他。不过,他拿着手里的钥匙一直觉得很纳闷,箱子已经存在旅馆了。这个男的后来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出名了,这个女的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去找他,他实在想不起来。女的很痛苦,就考到这个公司工作,甚至做了他的秘书,老启发他,可男的始终想不起来。经过若干年后,女的几乎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个男的一直没有结婚,他一直觉得有问题,有时候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钥匙,不停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的老启发他,说起医院出来的路上有一个咖啡馆,还去旅馆把箱子拿来给他看,他都若有所思。有一次,他自己沿着医院出来的路上一直走,走到他们两个曾经的家门口,钥匙往里头一捅,门开了。他回头一看,那女的也来了,他突然就想起来了,两个人拥抱,电影也就完了。
苏:典型的好莱坞制作,在1978年那可少见。
王:对呀。我挺喜欢看这部电影,后来我还重看过,我觉得《鸳梦重温》比《魂断蓝桥》还好看。这种艺术片感情描写得很真挚,很有意思。好莱坞的片子往往是通篇没有说教的成分,不讲大道理,但是人们看了之后,对美国社会印象都很好,说明他们的手法很高明。我们也可以学学这种手法,用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甚至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党和国家,宣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内部电影,当时可真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文化专制可过去了。那时候可没想这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什么的。解放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也看过美国电影,再加上我们这些干部好歹都有抵抗力,1978年再看看这些美国片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然后拼命去搞票,再有还要去看,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都是非常受欢覾-的。郭兰英一唱歌,什么《歌颂周总理》,哎呦,那个全场鼓掌啊,热泪盈眶啊,当时别提有多热闹、多感人了。那时候的文化生活,真正是人们的庆典一样。这和当时的物质生活是一个鲜明对照,1978年的物质生活还没有看到大的改善,物质供应什么的还是凭票。像我,特别爱吃花生米,能敞开吃花生米,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情了。我作报告老举这个例子,说我特别爱吃花生米,等到了一块四一斤的花生米敞开吃的时候,从我这点就证明,农村的问题解决了,能吃上饭了。花生米一块四一斤,价钱再上不去了,我这爱吃花生米的人随时能买到,说明物质丰富了。当然,这是以后了,1978年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时候安徽也才偷着干起家庭联产承包,北京这边可能更晚,因此供应还没好呢,物资不充足。但比文革期间稍好点。
苏:从文化上可以看出,人们当时比较兴奋。
王:尽管物质生活改变不大,但人们确实比较兴奋。一个是工作上很兴奋,我们能放开手大干了,没有人整我们了,可以搞现代化了,这是第一个兴奋。第二个兴奋是文化上的,我们这些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比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要高很多,所以,就觉得,总算不要整天听八个样板戏了,能看电影了,能看一些文艺演出了,特别是有一些文艺演出,能批判一下四人帮,歌颂一下周总理。那时候群众热烈的场面可不像现在唱通俗歌曲这种热闹法。郭兰英一唱《歌颂周总理》,那全场就是热泪盈眶啊,那种感情的真挚真是记忆深刻。
岔开讲一句,现在有些样板戏也老演,说实话,我认为有的唱腔艺术上是很不错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江青的烙印,心里不太舒服。
人们的文化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逛内部书店看内部小说。我记得当时出了很多内部小说,很多人都喜欢逛这些内部书店看看这些小说。我记忆中出了一批苏联的内部小说,我一度非常着迷,那一年我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将两大本厚厚的《朱可夫传》给看完了,写得真好,非常精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内部电影搞票比较难一点,文艺演出是公开的,稍微容易一点,但也得要票。虽然要票,但能看到的人比较多一些,我记得当年公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讴歌天安门事件中的人们,也挺好看的。想想1978年前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化生活的变化很大。
我们对文化生活是有需求的,我记得文革前,我们为了看电影、看演出都是到外面排队买票的,两个人带上孩子一起看电影、看戏,这是作为一家人很重要的享受。文革期间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文化上很苦闷,那时候觉得这种苦比物质生活的苦还难受。因为物质生活上,我们至少能吃饱饭,不像一些农民吃不饱饭,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的。1978年前后,当时也没什么电视,收音机里也听不到什么,但可以看内部电影、看文艺演出、看内部小说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喜悦的改变。
毛主席有没有错?
苏:当时你们思考的更高一点的政治话题都有什么?
王:那时候也有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对大的事情的思考。譬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韩伯平、储传亨等,已经开始有思考几个问题了。一个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对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怀疑?毛主席有没有错误?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只是不敢说而已,看不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正确性。我们也在关注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彻底地否定,还是三七开?或者几几开?这个我们比较关心。我们也有议论,都觉得文化大革命否定越多越好,这一点我们是私下议论比较多的。
对毛主席有没有错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三个方面想不通,心底自己起了怀疑,但不太敢说。第一是毛主席支持江青。我对江青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过好印象。江青在文革前就老来北京市指导工作,市委宣传部长李琪[9]坚持原则,没有理睬她的又打又拉。我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听到一些江青的事情,譬如说她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大家对她都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我心想: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后来文革发动,一直到文革结束,毛主席支持江青,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大家对江青的印象可谓坏极了,心想:毛主席怎么支持她?说实话,江青可给毛主席减了不少的分。
第二是林彪。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时,我正在牛棚,听了之后,心里就想:这个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跟我们党历来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完全不一样!心底就犯嘀咕,怀疑林彪这个说法,那时可不敢怀疑毛主席。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又说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我心底有些怀疑: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物,也会被骗?
第三,也是对毛主席是神的信念的最大动摇,就是再次打倒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搞全面整顿。那时我们可是非常热情的,一提起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我们就觉得劲都来了,还很兴奋地说:又要开夜车啦!可是,清华大学刘冰通过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两封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却被毛主席批评了,而且很严厉。[10]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迟群、谢静宜的印象都很坏,就觉得毛主席怎么了?
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使小平同志被诬为总后台,被完全打倒。我完全想不通,是不是毛主席老了?因为我接触到的人都热情地支持整顿,支持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再次打倒邓小平实际上是毛主席彻底脱离了群众,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我们私下里还传文化大革命的笑话,传江青的恶劣行径和处理情况,这都成为人们谈话很重要的一个热点。
苏:都有些什么笑话?
王:虽然过去30年了,我还记得一些笑话是关于军宣队的,当时军宣队在一些地方还没走,于是大家就传一些军宣队不懂行、说外行话的笑话,我记得那时候这种笑话比较多,至于说点白字什么的,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我记得一个笑话,关于军宣队训话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说成亡羊补宰也不晚,什么叫亡羊补宰呢,就是说现在再补宰一刀。(笑)反正当时类似这样的笑话特别多。当然,文革中,很多军宣队的干部是很不错的,很有原则,也有正义,这一点应该肯定。
传播笑话的同时,再有一个就是传对江青的处理,要不要枪毙啊什么的。还说张春桥是叛徒啊,康生怎么坏啊,因为当时对这些人还没作结论,我们这些人都议论这些。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毛主席?这些曾经是在某一层干部中小范围讨论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开呢,大家都在盼着,看中央怎么表态。
苏:当时您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什么看法?
王:1978年,大的问题还牵扯到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究竟是非标准应该怎么算?以什么为标准?我们这些人议论,以实践为标准,我们好像都是接受的。而对于两个凡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错了,我们怎么办?真理标准讨论,我们这层干部已经接触到了,但思想上并不是很清楚,更没有意识到这标志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标志着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都没有认识到这么高。
对毛主席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真理标准的想法,都纠结在一起,这成了我们思想上一个重大的扣。我们是倾向于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被否定,我们觉得毛主席应该也是有错误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讲,但是能不能这样做?最后中央到底作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都在底下猜测啊,议论啊,传小道消息啊,就处于这种阶段。我印象中,1978年就处于这种阶段。
谁都不好过
苏:您怎么看待文革期间的一些人和事?
王:现在想想,文革期间,谁都不好过。
刚才我说了这个时候小道消息很火。我们这些人朋友不少,兴趣也相投,互相之间可不是就谈论这些事情么。中央的事情,还有北京的事情,都在讨论之列。旧市委的一些干部当时对吴德的意见挺大的[11],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他对旧市委的干部执行左的东西,整得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他对天安门事件难辞其咎,而且他在当时还保持着不明朗的平反态度,这对当时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说是一个阻力。这是我听到的多数人的看法。
当然,后来我看到吴德[12]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这本书,我对他的看法也有变化。吴德也有他很难的一面,他在当时处于那样的地位也做了一些好事,也很不容易的。他跟江青他们保持着距离,后来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当时我们在底下体会不到,就觉得咱们是最先被打倒的,受了很多委屈。大家对李雪峰、吴德都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是来打倒我们的,所以有意见。对毛主席还不敢怀疑,怨气不敢发到毛主席身上。
1972年我从下放的地方门头沟区调回市里,在化工局任职。没多久,化工局要提拔我任副局长,结果到了市委被拦住了,市委那边的负责人明着就说:他是旧市委的人,不能提拔。化工局的党组书记黄光就和这个人吵架,说:我也是旧市委的人。当然,这次提拔没有成功。
我们当时觉得他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的[13],我们北京市委(指旧市委)怎么回事,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批人,结果,他们对待我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听汪家镠[14],他们到北京市委来,好像到了敌占区的感觉,那么一种心态。把我们都看成了敌人!
苏:为什么都看成敌人了?
王:也许他们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才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时也没敢怀疑到毛主席,毛主席是不能怀疑的。但他们这样对我们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又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然苦闷、怀疑,那你说我们怀疑到哪里去?当然就是怀疑到我们直接接触的这两个人。
最早是李雪峰来到这里,接管北京,他一来就把包括我在内的人都打成了黑帮[15],这些事情就是他做的。当时华北局工作组就在那里,像我这样的都当了黑帮,被专政了,更不要说那些高级干部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中下层干部都这样了,你这打击面也太广了吧。而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同属华北局,你难道不知道?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当时毛主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嘛。但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认为我们没什么错误,我们都是革命干部,怎么你们一来,我们都成了敌人了。哎,当时真的很苦闷,革了一辈子命,一片热忱,结果成了这样!
不过,我想,当时的那个处境,除去江青那批人好过之外,我看没有什么人好过。各有各的难过之处。李雪峰也不例外,他很快就被换掉,也被打倒。
苏: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林乎加同志来北京了。
王: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实干派。
吴德走了之后,1978年11月,林乎加[16]调了过来。林乎加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段呐,北京到处都传乎加指示,我们这批人是非常支持他的。我后来去了经委(时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陪着林乎加到处跑厂子,当时我对林乎加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都传说他在上海、天津干得很好。我觉得林乎加是实干派,当时北京就缺这样实干的领导呀。像我接触的旧市委的一批人,都是挺佩服林乎加的,而且都很支持他。
认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的呢?有一次,北京市科委的同志给他汇报,汇报完了之后,说希望林乎加同志给大家讲一讲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据说他生了气了,可能拍桌子还是怎么的了,反正生气了。说明他当时是比较支持华国锋的,支持两个凡是。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他怎么是这个态度?觉得这是不对的。开始对林乎加有怀疑,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后来林乎加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跟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吧,绝不是北京市的干部顶了他什么的。
其实,林乎加在北京是干了一些实事的。华国锋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用了很多外汇,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背上了包袱。林乎加在北京的时候,也提出要搞多少外贸,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没边了,有点过分了。不过,这说明他是很想搞经济、搞发展的,他是实干派。診-来对他真没什么怀疑,一度各地到处都传乎加指示。那时候他一个一个口到处听汇报,汇报完了他就讲话,他讲的话我们回去都很认真地传达,有一段我们都说,全北京市各口到处都在讲乎加指示,他的威信挺高,大家还是非常支持他的。
当时我在经委,对他就挺佩服的,他比较懂行,工作能力挺强,他愿意听工厂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挺懂。他也愿意和干部们交流,跟他说点思想上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听的。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一些什么感受?30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您有些什么印象?
王:1978年,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光是党内外的同志关心,普遍的中国人都关心,而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1978年是酝酿的一年、思索的一年,也是思想开始分野的一年。
当时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成型,人们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些想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四人帮那一套东西很不满,这是肯定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对于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又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说,1978年是思索酝酿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旧斗争的一年。
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两个方面的感慨,一个是没想到。1978年的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我没想到30年后我们国家有这么穃-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我们的步子都走得相当快。还是診-来的那些土地和人民,还是診-来那些资源,但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却成倍地增多,必须承认,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
第二个就是忧虑和反思。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物欲横流等诸多丑恶现象都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改革中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付出代价、交高额学费,但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上不太够,应该学习德国这个民族敢于直面的精神和勇气,从制度上、体制上总结这30年,特别是反思建国59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当然,要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还得几代人,急也急不得。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反思的不够,总结的不够,用的也不够。趁着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建国59年历史的人还在,应该好好总结和运用。我们民族一旦接受这笔财富,我们的民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强大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更是软实力的强大,我们现在似乎还缺这个!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