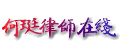司法改革方向何在
1269 人阅读 日期:2008-09-04 16:51:24 作者/来源:贺卫方
《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我的长篇访谈,题为“不走回头路”,对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之后,该报又发表了一系列持论各异的文章。其中陈忠林教授和何兵教授更多地强调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挽救目前走向误区的司法改革,而张千帆教授则明确地指出所谓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是走民主化抑或职业化的路径,我与何兵教授已经有过几个回合的商讨,甚至包括在天涯社区的“法律论坛”上一起与网友之间的交流,虽然所谓“理越辩越明”的效果并不明显。至于陈教授,我们已经商定不久的将来在重庆大学法学院开展一场辩论。我很高兴高一飞教授也参与其中,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老实说,都是我不大赞成的观点。包括高教授在内的几位作者都是我熟悉和尊重的学界同道和朋友,高教授对于西方法治和相关学说有着精深的研究,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却看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说和论证,本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我在这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以就教于高教授(以下就称他“一飞”)和读者诸君。
避难就易何处避
关于司法改革的方向,一飞明确地表达了一种避难就易的思路。在文章里,他认为过去十年来的司法改革所指向的弊端是所谓三化——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管理的行政化以及司法官员选任的非职业化,但是他说这样的改革是一种方向性的失误,因为那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岂是法院能够推得动的?不如在现有框架下,在程序上寻求司法公正之道。他提出的一个构想是集中审判,案件一旦开审就将法官完全封闭起来,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甚至不能回家,“由法警监督到特定旅馆休息”直到作出判决。如此则外部干预便无从下手,判决的公正性就得到保障。
这个思路很怪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封闭法官的做法。也许一飞是受到了英美国家陪审团的做法的启发。但是,陪审团跟法官却是完全不同,它的成员是从社会随机选任,每案一组,案件审理期间的确不与外界接触(周末当然可以回家),但是案件审理完毕他们就离开法院,生活和工作也都恢复正常。但是法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都在审理案件,对他们全封闭,则势必把法官都变成没有家庭生活的僧侣阶层。这种极端化的做法哪里具备一点可行性呢?
一飞的另一个技术层面的改革主张是强化民众对于法官选任和监督的参与。例如组成由律师和民众代表参加的法官提名委员会提名法官,交由人大任命。不仅如此,人大还要对法官进行定期考核,以决定是否留任。另外,他还提出要对于司法考试制度进行改革的思路,还有借鉴治安法官的设想,可惜对于前者,他的方案缺乏合理论证;对于后者,他根本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该如何借鉴。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改革真的就与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没有关系了么?果然就是一个程序的变革,像一飞轻松地说的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决定么?集中审理涉及诉讼法的剧烈变动,没有全国人大对于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最高法院院长就可以直接修改?如果不能,那么人大修改法律就是一个政治的过程,想绕过这个“红灯”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设置民众代表和律师组成法官提名委员会,分割人大和法院的权力,这也毫无疑问属于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之,一飞所指责的妨碍司法公正并且需要改革的几大因素——“法官由官方任命,媒体报道受到多种限制,民间的考评机制不存在,民众反映的问题法官难以受到查处”,凡此种种,哪一项仅仅是个程序变更,跟政治体制没有深刻的关联?我的看法,如果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问题,作为学者,不应该主张避难就易,因为那根本是回避不了的,反而应当努力地推进不利于司法公正的政治体制的变革。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司法改革的书里,我引用了《西游记》第五十九回里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用在这里表达我对于如何走出困境的看法:
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运送正义的方式》自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道德考察怎样察
由于司法表现不彰,不少人都在寄希望于在选任中强化对司法官员的道德考察,一飞在文章里也明确地批评以往的司法改革存在着“重法官的业务素质而轻道德素质”的偏差。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怎样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一飞却语焉未详。这跟陈忠林教授的情况一样,陈教授强调“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对于法官进行“良心教育”,但是这“三常”以及“良心”的含义如何,如何进行良心教育,用怎样的标准考察某个法官的良心教育已经“修业合格”,终究不明就里,颇给人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感觉。
自然,这也不是一个新困难。汉朝兴察举孝廉,以选拔孝敬父母、廉洁奉公的“德才兼备”之士担任官员。效果呢?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后来之所以采纳科举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一般的道德考察无从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道德高洁之士,反而给腐败留下巨大空间,导致社会伪善盛行,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主要以一个人对于古典道德学说把握的娴熟程度和分析问题的条理为考察指标。实际上,一部科举取仕的历史充分表明,通过这种方式效果仍然是差强人意,从民间对于官府的普遍不信任、官员的全面腐败、“仁义道德”与“男盗女娼”之间剧烈的反差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德治”正应了司马谈评六家要旨对儒家的那句考语:“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且历史上所发生的残忍的杀戮迫害往往是那种自我标榜的道德君子所为。我国历史上酷刑延绵不绝,跟儒家的高调道德也是密不可分的。钱锺书先生的话耐人寻味:“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着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谈教训》)
所以,任何健康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尊重人性基本趋向的基础之上的。良好的司法制度也是如此。在制度的设计上,我们首先要以法官也是人为前提,需要对于他的正常欲望有合理的保障,而不可以像庄子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例如,我们需要提升法官的选任标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职位的崇高。需要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从而让法官成为人们心目中有尊严的职业。需要给他们的职位提供严格的保障,确保他们独立裁判案件,不受一切法律之外的干预。需要让他们珍惜自己的职业前途,看重自己的社会评价,从而形成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群体。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法律人注重职业伦理的建设,这正是法律职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职业伦理,跟宽泛的道德不同,它是社会分工发育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职业群体,逐渐地就会形成这个群体成员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守则。这类准则虽然不是法律,但是,由于变成了每一个成员的内心确认,同行之间对于它们的分享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它们成为不假外力便可以有效实施的规范。违反者它们的个别事例当然也会出现,但是整体而言,职业伦理是保证司法职业良好表现的重要条件。
不妨列举一下美国加州司法伦理准则的内容,以为参考。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五项戒律:一、法官应维护司法的公正与独立;二、法官应避免从事不正当或表面上不正当的活动;三、法官应公正、勤勉地履行司法职责;四、法官从事准司法和非司法活动,应使其与法官义务产生利益冲突的风险降至最低;五、法官和法官候选人应避免从事不当的政治活动(参看Brian Kennedy,《美国法律伦理》,郭乃嘉译,商周出版,2006年,页260)。表面看来,内容似乎相当简单,但是,每一条所附加的详细说明以及有关案例却显示它们明确的范围和严格的效力。例如,如果法官单方面与当事人接触,即便没有任何收受好处的行为,也可能受到依据第二条的指控;一个在法庭上诋毁律师人格的法官足以因为第三条戒律而遭到公开警告或公开谴责,结果失去继续担任法官的机会。在我国,虽然最高法院也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但是内容简陋,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实施机制,不免流于一纸空文。
一飞在文章里提到的监督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于法官,还是其他行使公权力的群体,切实有效的监督离不开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司法领域,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庭审过程的真正开放、司法判决的说理清晰以及全部判决书向全社会公开。这方面我们的司法实在是相距太远。试想,连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都不全部、全文地向公众展现,人们想监督又怎么可能?另外一个要件是新闻自由,不过这又是大的体制问题,按照一飞的观点,也是要回避的问题。奈何,奈何。
正路坎坷赖坚持
在历时近二十年之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应该说,之所以出现一些对于过往改革的争议和非议,也是事出有因的。在中国这个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通过引进西方模式建构自家的现代制度仅仅只有一个世纪,其间又经常受困于救亡图存与启蒙建制、中西古今、秩序与自由等等之间的紧张。我们这一代人居然有30年的和平时期用于对于法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无疑已经是相当不易的事情。但是,从计划经济那种非法治的窠臼里摆脱出来,观念中的是非曲直的厘清本身需要非常艰巨的努力。即便在今天,看看网络上的言论,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怀念改革开放前的体制,我们就知道期望现代制度能够一蹴而就地建成,确实太过于异想天开了。
不仅如此,改革本身即便都是从良好的初衷出发,所设计的方案也会有不周全的地方,理想与现实之间会有落差。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南辕北辙,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怀孕的是大山,生下的是老鼠。在前改革时代,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制度的相互作用、文化的不同因素之间有着某种平衡,改革的过程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给人心理带来冲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就曾分析过欧洲其他地方农奴制盛行却社会稳定,法国给农人自由却引发最激烈革命的吊诡现象。所以,对于改革家来说,只有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对于国家历史、国民情感、域外经验等的广泛研究。需要审时度势,对于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作出合理的安排。需要系统的眼光,在设计整体的时候注重局部的价值,从事局部工作的时候,关注它们与整体之间的呼应和互动。此外,还需要具有反思精神,发现问题时能够理性地检讨,听取不同意见,采取有效的平衡或改进措施以确保改革本身尤其是方向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当然,目前发表反思司法改革文章的都是学者,而不是实际改革的决策者。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过去曾经十分频繁的官方与学界之间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近年来已经大为减少,这导致了双方信息交流的不畅,甚至出现某些不大友善的想象。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一飞的文章释放出足够的善意,力求在官方话语的框架内保持学界的参与,对此我并不反对,甚至乐见学界中人的这种沟通努力。不过,这也是所谓戴着镣铐跳舞,期间分寸的拿捏需要很高超的艺术。我觉得,一个底限是,策略的考量不能失去学术本身的独立性。
眼下这场讨论也可以看作是一次阶段性的反思。对于过去的改革措施,也许我们应当更具体地加以分析,例如有人说某些改革的倡导者存在着盲目崇拜西方司法理念的倾向,我们需要细致地看是那些主张存在着这样的偏向,所谓西方理念反映的是否属于司法制度的普适逻辑。有人主张司法民主化,这当然很好。不过,要追问的是,严格地适用反映国民意志的法律是否正是司法民主化的第一要求?那种要求法官审理案件时可以在法律之外对于什么是人民利益和人民要求作出判断,并把这种利益和要求作为判案准则,是否反而让法官有了规避法律、翻云覆雨的机会?过去的改革一般主张司法应当通过更消极的方式确保法院的中立性,但是现在有人又在倡导恢复“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否需要把那种审判方式的含义和利弊得失进行更透彻的分析,把今天跟陕甘宁边区之间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差异具体地加以描述,从而让我们知道审判方式与社会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大而化之的空泛言辞,而不是深入细致的理性论证。
如前所述,在我们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绝对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许多坎坷或曲折也许来自于耐力不够。一旦看到改革出现某些弊端,就愿意回到老路上去,一些改头换面的旧方法就沉渣泛起。其实,沿着合理的方向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也许就峰回路转,光明的前景就出现了。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这样的毅力,以至于总是在循环,走了很长的路,发现还在原地。姑且引用一飞的一位著名乡人的话为本文作结:
“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相关链接: